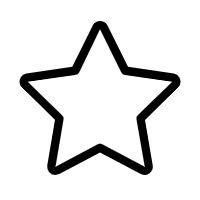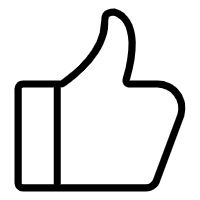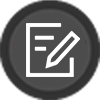拜伦
荡荡万斛船,影若扬白虹。 自非风动天,莫置大水中。 今天早上,我的书桌上散放着一垒书,我伸手提起一枝毛笔蘸饱了墨水正想下笔写的时候,一个朋友走进屋子来,打断了我的思路。“你想做什么?”他说。“还债,”我说,“一辈子只是还不清的债,开销了这一个,那一个又来,像长安街上要饭的一样, 你一开头就糟。这一次是为他,”我手点着一本书里Westall①画的拜伦像(原本现在伦敦肖像画院)。“为谁,拜伦!”那位朋友的口音里夹杂了一些鄙夷的鼻音。 “不仅做文章,还想替他开会哪,”我跟着说。“哼,真有工夫,又是戴东原②那一套。” ———那位先生发议论了——“忙着替死鬼开会演说追悼,哼!我们自己的祖祖宗宗的生忌死忌,春祭秋祭,先就忙不开,还来管姓呆姓摆的出世去世;中国鬼也就够受,还来张罗洋鬼! 俄国共产党的爸爸死了,北京也听见悲声,上海广东也听见哀声;书呆子的退伍总统死了, 又来一个同声一哭。二百年前的戴东原还不是一个一头黄毛一身奶臭①Westall,通译书斯托尔(1765-1863).英国画家。②戴东原,即截震(1724--1777)清代学者。对经学、语言有重要贡献,被称为一代考据大师。一把鼻涕一把尿的娃娃, 与我们什么相干,又用得着我们的正颜厉色开大会做论文!现在真是愈出愈奇了,什么,连拜伦也得利益均沾,又不是疯了,你们无事忙的文学先生们!谁是拜伦?一个滥笔头的诗人,一个宗教家说的罪人, 一个花花公子,一个贵族。就使追悼会纪念会是现代的时髦,你也得想想受追悼的配不配, 也得想想跟你们所谓时代精神合式不合式,拜伦是贵族,你们贵国是一等的民生共和国,哪里有贵族的位置?拜伦又没有发明什么苏维埃,又没有做过世界和平的大梦,更没有用科学方法整理过国故, 他只是一个拐腿的纨挎诗人,一百年前也许出过他的风头,现在埋在英国纽斯推德①(Newtead)的贵首头都早烂透了,为他也来开纪念会,哼,他配]讲到拜伦的诗你们也许与苏和尚②的脾味合得上,看得出好处,这是你们的福气——要我看他的诗也不见得比他的骨头活得了多少。 并且小心,拜伦倒是条汉,他就恨盲目的崇拜,回头你们东抄西剿的忙着做文章想是讨好他, 小心他的鬼魂到你梦里来大声的骂你一顿!“ 那位先生大发牢骚的时候,我已经抽了半支的烟,眼看着缭绕的氲氤, 耐心的挨他的骂,方才想好赞美拜伦的文章也早已变成了烟丝飞散:我呆呆的靠在椅背上出神了;—— 拜伦是真死了不是?全朽了不是?真没有价值,真不该替他揄扬传布不是? 眼前扯起了一重重的雾幔,灰色的、紫色的, 最后呈现厂一个惊人的造像。最纯粹,光净的白石雕成的一个人头, 供在一架五尺高的檀木几上,放射出异样的光辉,像是阿博洛③给人类光明的大神,凡人从没有这样庄严的“天庭”, 这样不可侵犯的眉宇,这样的头颅,但是不,不是阿博洛,他没有那
①纽斯推德,通泽斯泰德,是一处修道院庄园,原为拜伦家族的领地。②苏和尚,即苏曼殊(1884—1918),近代作家、艺术家,早年留学日本,后为僧。他翻译过拜伦的作品。③阿博洛,通译阿波罗,希腊神活中的太阳神.
样骄傲的锋芒的大眼,像是阿尔帕斯山①南的蓝天,像是威尼市②的落日,无限的高远,无比的壮丽,人间的万花镜的展览反映在他的圆睛中,只是一层鄙夷的薄翳;阿博洛也没有那样美丽的发鬈,像紫葡萄似的一穗穗贴在花岗石的墙边;他也没有那样不可信的口唇,小爱神背上的小弓也比不上他的精致,口角边微露着厌世的表情,像是蛇身上的文彩,你明知是恶毒的,但你不能否认他的艳丽;给我们弦琴与长笛的大神也没有那样圆整的鼻孔,使我们想象他的生命的剧烈与伟大,像是大火山的决口…… 不,他不是神,他是凡人,比神更可怕更可爱的凡人,他生前在红尘的狂涛中沐浴,洗涤他的遍体的斑点,最后他踏脚在浪花的顶尖,在阳光中呈露他的无瑕的肌肤,他的骄傲,他的力量,他的壮丽,是天上磋奕司③与玖必德④的忧愁。 他是一个美丽的恶魔,一个光荣的叛儿。
一片水晶似的柔波,像一面晶莹的明镜,照出白头的“少女”,闪亮的“黄金篦”,‘陕乐的阿翁”。此地更没有海潮的啸响,只有草虫的讴歌,醉人的树色与花香,与温柔的水声,小妹子的私语似的,在湖边吞咽。山上有急湍,有冰河,有幔天的松林,有奇伟的石景。瀑布像是疯癫的恋人,在荆棘丛中跳跃,从嶝岩上滚坠;在磊石间震碎.激起无量数的珠子,圆的、长的、乳白色的、透明的,阳光斜落在急流的中腰.幻成五彩的虹纹。 这急湍像是一颈的长鬣,一阵阵的瀑雷,像是他的吼声。在这绝壁的边沿的顶上是一座突出的危崖,像一个猛
① 阿尔帕斯山,通译阿尔卑斯山.#p#副标题#e#

 943
943
 0
0  0
0